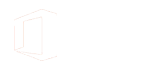清代天文学家李锐......
大卫·邵乐思的治学和建树:纯粹探索凌绝顶
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大卫·邵乐思,邓肯·霍尔丹和迈可·科斯特里兹,以表彰他们对“物质的拓扑相变和拓扑相领域的理论性发现”。本文作者曾是邵乐思的博士后,文章主要概述邵乐思在物质相变方面和其他领域的主要成就,对获奖工作进行了解读;他与邵乐思学习、研究的一些经历,以及对其独到治学风格的感悟。(本文将Thouless译为“邵乐思”,取自发音并中国化:“姓”同我国古代哲学家邵雍,他们都“乐思”。)
撰文 | 敖平(上海大学定量生命科学国际研究中心和物理系,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
大卫·邵乐思(David J. Thouless)对很多重要物理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在同行中有理论物理学家中的理论家称誉。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他和邓肯·霍尔丹(F. Duncan M. Haldane)、迈可·科斯特里兹(J. Michael Kosterlitz),对他们物质形态及其转化探索的嘉奖实至名归,从物理学本身的发展状况表彰时机也很恰当:相应领域正处于蓬勃发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奖工作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但对邵乐思却是迟来的荣誉。他在物理学的其他领域也做出了很多原创、杰出的贡献。我有幸就教于邵乐思,并在他身边工作多年, 在这里从一个后学的角度试图理解得奖工作在物理学和科学中的意义,对邵乐思的治学风格记述一些个人的观感,希望对当下我国的科学研究者有所启示。
物态转变是自然界中的普遍现象。获奖的主要工作是预测一类相变,即拓扑相变的存在,这是人类已知的第三类相变。人类对相变即物质形态之间的变化并不陌生。可以肯定地说从文明曙光出现,人类就理解第一类相变,至今已约10万年,现在称为不连续相变。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开水在沸腾下变成蒸汽,液体到气体的转变。在温带和寒带地区人类还应该明了冰块受热溶化成水,固体到液体的转变,这是另一个著名的第一类相变例子。第二类相变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直到工业革命时期,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研究如何提高蒸汽机效率的过程中发现,在足够高的压强和温度下,水与蒸汽的区别消失了,即连续相变。而拓扑相变则发现于当代,首先由理论预见[1]。
科学是要理解现象并发现其中的规律,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最重要的一步是建立逻辑自洽的定量理论,克服日常语言描述的模糊性,让科学理论更具有预测能力,更能指导科学实验和应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描述相变的定量物理理论基础是统计力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统计力学是我们目前适用范围最广泛的物理理论,超过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像许多其他科学理论,它的建立也经历了一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始于19世纪中叶研究没有相变的理想气体。代表性的物理学家有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和吉布斯。最重要的结果是发现了配分函数和正则系综,总结在吉布斯1902年的《统计力学的基本原理》[2]。20世纪初期,玻尔兹曼的学生Ehrenfest提出可用配分函数来描述相变,很长时间物理学界不相信这个提案, 理由之一是配分函数看上去像一个很光滑的函数,似乎不可能产生不连续。1933年Ehrenfest的学生Kramers建议取热力学极限来实现建立配分函数的不光滑,从而有描述相变的可能。1944年Onsager找到第一个严格的例子,1952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厘清了热力学极限的物理含义,其结果通常称为李-杨定理。至此,第一类相变,不连续相变的完整定量理论描述才建立: 从实验观测到理论建立用了近万年。而连续相变的完整理论直到1971年才由Wilson完成,同时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Fisher、Kadanoff、Pokrovsky和Widom。从现象到恰当理论建立用了约150年。至此,统计力学描述相变的完整理论框架才完成[3]。
运用统计力学和最新的理论进展,邵乐思和科斯特里兹在1973年Journal of Physics C论文[1]中预测了第三类相变,即拓扑相变的存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物理系统——二维超流膜——可能会实现这个相变。它的物理图像是量子涡旋和量子反涡旋对的分离:低于相变温度量子涡旋总是成对,黏滞系数为零,超流存在;高于相变温度,有自由的量子涡旋和反涡旋,黏滞系数不为零,超流不存在。从自由能F的角度,这是涡旋的能量E与它的熵S竞争的结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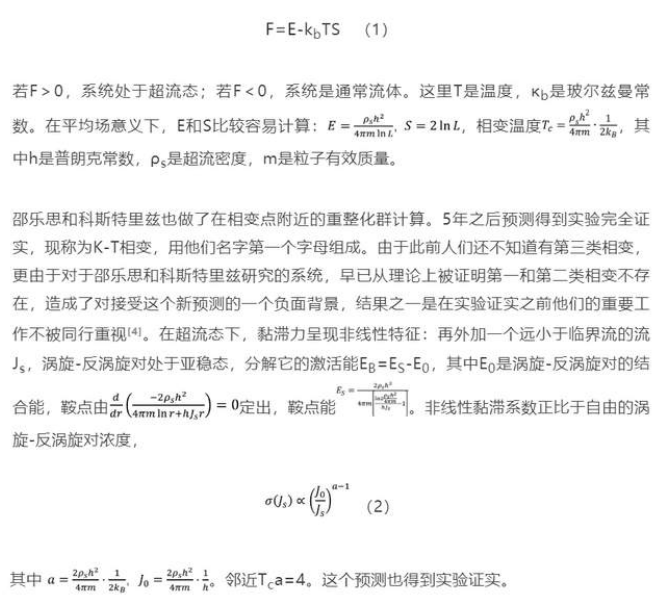
邵乐思、霍尔丹和科斯特里兹的探索显然加深了人类对物质形态和它们之间转化的认识。自然界中物质形态多姿多样、千奇百怪。物质的组分和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通过统计力学能描述这些形态及其相互转换,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微观到宏观、由组分到其涌呈现象的过程。目前我们只知道不连续、连续和拓扑共3类相变,这个数目小于已清楚的基本作用力的数目——相反方向的、把系统分成更小部分的微观物理现象探索,有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共4种。他们的工作有力地揭示了物理规律深刻的简单性和统一性。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拓扑相变对应领域已从个别物理学的探索变成了一个主流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表明它也有巨大应用前景,对新材料的开发和器件的发展,包括计算机,会有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相关工作也非常出色[5]。从相变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首先,理论完全可以走到实验前面,甚至指引着实验前进;其次,它表明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并和应用研究有出人意料的相互促进。第一类相变是实验和应用完全走在理论前面,但理论对设计新的复合材料及其他应用有指导。第二类相变是典型的理论-实验相互促进,而第三类相变则给应用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的宝藏还等待着被发现。
在本文中对邵乐思的贡献作一个全面的介绍是不可能的,但除了在拓扑量子数方面的工作[6],至少我应该再简单介绍他的另外两种成就。邵乐思是把量子多体理论运用到核物理的先驱者之一[7],在这过程中他也发展了多体理论,总结在他的专著中[8]。邵乐思在凝聚态物理输运过程中的局域现象上做出承先启后的贡献。Anderson和Mott各自提出了关于局域现象的理论模型,之后近十年他们不能准确地理解对方的工作。同时又有新的理论模型与Anderson和Mott的理论不一致。邵乐思的同事们,包括Mott,认为他能澄清这个理论混乱,敦促他研究局域现象。不负众望,邵乐思从Bethe-Peierls方程出发建立一个严格理论,证明Anderson和Mott是对的[9]。
在关键的几个科学研究阶段,我非常有幸受到邵乐思的言传身教和直接帮助。1990年初和博士导师 Leggett讨论我博士后的可能选择,许多有名的地方他认为不适合我,西雅图的邵乐思却是他的推荐之一。正巧得知邵乐思要到邻近州的一个大学去做学术报告,我就开车去听他的报告。报告后我给他介绍了我的博士阶段的工作和今后的打算。他觉得尚可,让我回去后请我导师给他寄封推荐信。一个月后他让我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物理系做一个面试报告。像很多年轻研究者,我在报告中过度呈现技巧和细节,对整体物理讲解不够,被问得张口结舌,头晕脑胀,好像不能自圆其说,很紧张。报告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继续就我没回答清楚的地方提问。这时我已清醒过来,给出了条理清晰的论证。然后他说,你现在的表现比你一个小时前好得太多。
1990年底,我到西雅图做邵乐思的博士后。开始尝试几个题目,要么他不满意,要么我不满意。有一天,我对他说,我想研究量子拓扑缺陷,如涡旋动力学。他想了一会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方向,但很难,你得准备下功夫。难点之一是,不是没有量子涡旋动力学理论, 而是很多,但没有一个能一致地解释相关实验现象,如已有近30年的第二类超导体中的反常霍尔效应,大家不知原因在哪里。接下来的两年我就研究各式理论,理解各种相关实验现象。我们的结论是,实验观察没有问题,但现有量子涡旋动力学理论要么不完整,要么有错。我们得重新建立理论。最终从微观理论得到的运动方程类似于一个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动力学方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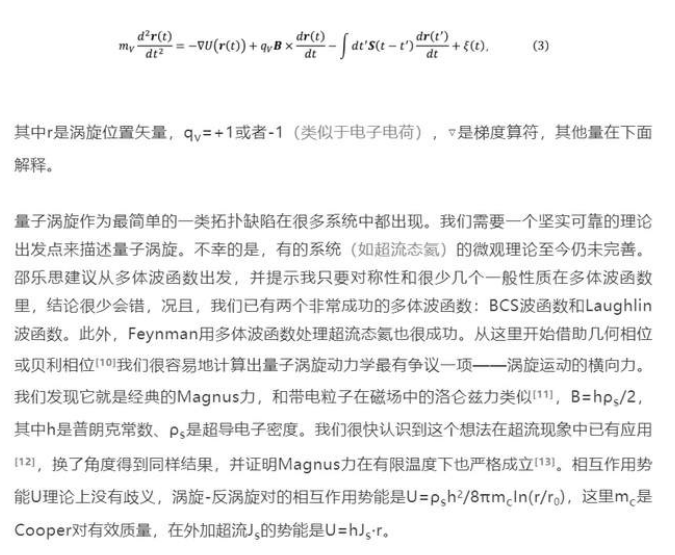
量子涡旋的运动很奇怪。我和邵乐思研究了它在二维空间中的一般量子隧道效应[14]。方程(3)可以用Leggett的宏观量子效应方法转换成对应的哈密顿量,它是一个高维问题,适合用路径积分来处理。另一个令人疑惑的是关于有效宏观波函数遵从的运动方程。超导体和超流体都能用多体波函数描述,它们都有有效宏观波函数,但遵从对称性不同的方程:超导体是当时公认随时变化Ginzburg - Landau方程,而超流体是所谓的非线性薛定谔方程。我们需要证明超导体中超导部分的有效宏观波函数实际上也遵从非线性薛定谔方程。在Aitchison和朱晓梅的帮助下我们做到了:必须包括一个容易丢掉的对称项[15]。我们和牛谦一起,用多体波函数证明量子涡旋的“裸”质量是有限的,可能还很小[16-18]。我们发现涡旋和声子的藕合会导致量子涡旋的运动会是耗散的,并估算出耦合项[16]。牛谦是邵乐思的学生,当时刚成为助理教授,经常利用假期回到西雅图和邵乐思一起工作。邵乐思不但对他的学生和博士后很爱护和提携,对其他年轻学者也一样。
有一天,邵乐思给我一个预印本,一个著名俄国学者的最新工作。这个学者声称证明了量子涡旋运动的横向力几乎是零:另一个拓扑效应,能谱流动,几乎抵消贝利相位。邵乐思希望尽快听到我的意见。我用了一天一夜搞明白了这个学者的论证,认为他搞错了。第一,他确实发现了量子涡旋运动拓扑效应的一个新表示。但是,在量子涡旋运动中能谱流动完全等价于贝利相位,它们是同一物理现象的两种不同描述: 贝利相位是广延描述;能谱流动是局域描述。这在量子霍尔效应中已发现类似描述:Laughlin多体波函数是广延描述;Landauer - Buettiker局域边沿态描述。两种描述可以用Stokes类型的定理联系。第二,这个学者声称抵消会不完全,由一非拓扑量称之为驰豫时间所控制,这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邵乐思同意我的意见,告诉我以后要用微观理论明确地演示这种等效。我完成这项任务几乎是5年以后[19],在我建立反常霍尔效应模型[20]以后,早已离开西雅图[注1]。几年以后我在瑞典遇到这位俄国学者,我告诉他自己对能谱流动的看法,他当时同意我的意见,并认为在最近的一个实验中[21]可能已间接地观察到,在实验误差范围内B=hρs/2。邵乐思对我们的量子涡旋动力学工作很满意。他告诉我在他心中近30年的疑惑得到了回答,并认为我们关于量子涡旋Magnus力的工作是多体物理中有限的严格结果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发现新兴的系统生物很有意思。里面的复杂生物和医学现象,如癌症、发育、代谢等,很有物理中多体问题的特征,只是更不容易有定量描述,很有挑战。我告诉邵乐思我打算研究系统生物。他听了之后非常支持,同时安排我在华盛顿大学物理系作兼职副教授,给物理系学生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我在系统生物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随机过程结构,我怀疑这个结构在任意维数都是成立的,但它在数学上没有被人讨论过。一维很容易证明我是对的,很快也证明我的想法二维也成立,然后卡在三维。有一天他问我有什么新的问题,我就告诉他我最近碰到的难题,他说可以帮忙。因为他刚好有一个以前的韩国学生来访问,这个学生也对生物问题感兴趣。说不定我们一个前学生和前博士后就把问题解决了。遗憾的是我们试了近一年依然不能突破三维,但计算机模拟计算表明我的想法可以在高维成立。这引起邵乐思的好奇。他让我们给他讲讲近一年的努力,并让我讲讲在生物上为什么我的想法会正确。听完后他认为我的期望可能太高,但他可以来试试。不到两个星期,他告诉我他解决了,我的期望是对的,可以在任意维数成立[22]。现在这个结果是我很多应用的基础,如生物演化理论[23-35]和癌症产生与发展的理论[26-28]。邵乐思也告述我他认为我所发现的是一个巨大理论的一部分,十多年后的现在我们及其他研究者还没有完全完成相关的探索[29]。
从前面的讲述读者已能感受到邵乐思的为人。在做学问和培养年轻人方面,有几点我想再多着墨几笔,也许对改进我国目前的科研状态有一定意义。
独立思考。邵乐思对事物喜欢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诚实地对待物理,对待同事和他自己。在科学报告会上,在讨论中,他会如实地、有根有据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看法,直指核心,没有人们常见的客套。由于他学问的深度和高度,他很容易就能看到隐蔽的不足之处甚至错误所在。这对一些人是一个灾难,对更多的人却是一个学问精进的机会。他对自己也一样, 偶尔也有搞错的时候,他会认错。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形,我有些吃惊。他反而给我解释道,这个问题你已思考了几个月(事实我思考了不止一年),你不能指望我一个小时就搞对。
好奇敏感。好奇的例子前面已给一个。邵乐思是一个富有平等精神的人,他对各种歧视很敏感,很不喜欢。我女儿出生在西雅图,满月后,他夫妻来看望,送我女儿一本画册。他夫人说,大卫在书店里挑了很久,觉得这本内容比较平衡,有欧洲、东亚和非洲等小孩。这本画册我女儿还收藏着。
专注彻底。邵乐思对工作非常专注,对问题喜欢探索到它的逻辑终点。我想这种精神引导他和科斯特里兹发现拓扑相变,为物理研究打开了一道新的大门。诺贝尔奖委员会引证了他的一个1982年工作。他一直在研究其中的问题,世界上大概只有一双手都数得过来的研究小组在研究它,大多还与他有直接学术传承关系。大家都觉得他钻了牛角尖。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贝利问他为什么还在研究这个问题,邵乐思想了想,淡淡地回答说,这像珠穆朗玛峰,它在那里。老实地说,当时我希望听到一个“热血沸腾”的论证,对这个平实、简洁的回答是有点失望。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特别容易过度拔高自己的工作。有意思的是,在他的Topological Quantum Numbers in Nonrelativistic Physics一书中[6],他并没有收录这篇1982年的论文,而是一篇不是他写的论文,他认为该论文把问题和过程表述得更清楚。这本著作是进入该领域的非常优秀的参考书,我个人认为是必读。
学养厚实。他的学术修养非常深厚,不管是物理还是数学。他的基础训练非常扎实。我反思过我和他的前学生为什么不能突破三维,我发现是我学到的常微分方程理论太浅。在研究量子涡旋动力学时,我感觉用弛豫时间近似处理拓扑效应有问题,但一直找不到抓手:这个近似在凝聚态物理及其输运过程中应用广泛,很多情况下也很成功,似乎不可能有根本性问题。他建议我去重新研究Green和Kubo是如何建立输运理论的,在重读原始文献中我才注意到这些先驱者已经知道弛豫时间的局限,有时甚至会引起定性错误。经过反复思考,我和朱晓梅找到一个不用弛豫时间近似的方法同时计算了量子涡旋的拓扑效应和耗散效应:贝利相位和摩擦系数,并显式地演示了贝利相位与能谱流动的等效[19],计算出摩擦或耗散的相关函数S(c.f.方程(3)),同时也讨论了相关函数S和随机力ξ的关系——涨落-耗散定理:<ξ(t)ξτ(t)>=2S(t-t'),其中<···>是对随机力的平均,τ是转置。如果是高斯白噪声,S(t-t')=ηδ(t-t'),其中η就是摩擦系数。这个方法最近在研究冷原子系统中孤子的有效量子运动时被重新发现[30]。
心怀实验。邵乐思总是跟我说,当我们构造一个物理理论时,至少要想到该理论原则上的实验检验手段。如果它原则上不能被检验,那就不是一个物理理论。我想正是这个理念让他的许多工作走在实验的前面。我也有一个实验提案检验他的1982年工作[31]。由于对实验条件要求较高,据我所知迄今对这个提案还没有明确实验结论。我们也讨论了涡旋的一个量子拓扑效应的实验检验[32]。
学术传承。创新工作很少是凭空出现的。适当的传承和良好的环境很重要。邵乐思的博士导师是Bethe,Bethe做过Fermi的博士后,Fermi跟Ehrenfest学习过,等等。Fermi和Ehrenfest都是当时公认优秀的物理学导师。Bethe知识渊博、科学判断力强,写了凝聚态物理的第一本教科书,提出恒星如太阳演化的标准模型。他们发表的成果只是他们思考过的科学问题中的一部分。邵乐思当时的工作环境是Peierls所营造,是当时著名的物理研究中心,加上英国近代一直对学术研究的宽容,我们都知道她收容了马克思,《资本论》是在英国基本上完成;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她也收容了Bohm,这让我们有Aharonov-Bohm效应,一种著名的拓扑效应;她回收没找到国外进一步博士后的Kosterlitz,让他“捡到”一个物理学诺贝尔奖。邵乐思告诉过我他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在思考相变相关问题,70年代初和Anderson的讨论对他拓扑相变想法的发展帮助很大,Kosterlitz的加入对研究非常给力。
邵乐思30年前来过中国,我的一些国内朋友还记得他的尖锐问题。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中国工作过,其中一个儿媳是华裔。我回到上海交通大学后曾邀请他和夫人再到中国访问,告诉他中国已有巨大变化。他原则上同意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细节问题以致这个邀请计划没有在国内通过。也许以后我们可以再试着邀请他到我国访问。
我国传统主流之一的儒家文化鼓励中庸,不鼓励刨根问底、为规律而规律,我想邵乐思的榜样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独立思考、自信工作,让学术研究成为与经世致用和道德艺术平行的追求方式。这些是目前我国在文化发展上,特别在科学研究中,相当缺乏的。这对我们在突破思想樊篱、孕育科学创新中又多了一些助力。
注释
[1] 二十多年后有了漂亮的反常霍尔效应数据,但实验者竟没有认识到到他们的结果是我预测的一个定量实验验证。仔细分析请见:
Guo Chen Ao(2002) Physical Review B
https://journals.aps.org/prb/abstract/10.1103/PhysRevB.106.104507
参考文献
[1] Kosterlitz J M, Thouless D J. Ordering, Metastability and phase transitions in two-dimensional systems. J Phys C, 1973, 6: 1181–1203.
[2] Gibbs J W. Elementary Principles in Statistical Mechan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2. [吉布斯. 毛俊雯译. 统计力学的基本原理.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6]
[3] Brown L M, Pais A, Pippard B. Twentieth Century Physics. New York: CRC Press, 1995. [布朗, 派斯, 皮帕. 刘寄星译. 二十世纪物理学(第1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4] Kosterlitz J M. Commentary: the early basis of the successful Kosterlitz-Thouless theory. J Phys Condens Matter, 2016, 28: 481001.
[5] He K, Wang Y Y, Xue Q K. Quantum anomalous Hall effect. Natl Sci Rev, 2014, 1: 38–48.
[6] Thouless D J. Topological Quantum Numbers in Nonrelativistic Physic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98.
[7] Ring P, Schuck P. The Nuclear Many-Body Problem. Berlin: Spring-Verlag, 1980.
[8] Thouless D J. The Quantum Mechanics of Many-Body Systems. New York: Dover, 2014.
[9] Thouless D. Anderson localization in the seventies and beyond. Intl J Mod Phys B, 2010, 24: 1507–1525.
[10] Shapere A, Wilczek F. Geometric Phases in Physic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89.
[11] Ao P, Thouless D J. Berry’s phase and the Magnus force for a vortex line in a superconductor. Phys Rev Lett, 1993, 70: 2158–2161.
[12] Haldane F D M, Wu Y S. Quantum dynamics and statistics of vortices in two-dimensional superfluids. Phys Rev Lett, 1985, 55: 2887–2890.
[13] Thouless D J, Ao P, Niu Q. Transverse force on a quantized vortex in a superfluid. Phys Rev Lett, 1996, 76: 3758–3761.
[14] Ao P, Thouless D J. Tunneling of a quantized vortex: Roles of pinning and dissipation. Phys Rev Lett, 1994, 72: 132–135.
[15] Aitchison I J R, Ao P, Thouless D J, et al. Effective lagrangians for BCS superconductors at T=0. Phys Rev B, 1995, 51: 6531–6535.
[16] Niu Q, Ao P, Thouless D J. From Feynman's wave function to the effective theory of vortex dynamics. Phys Rev Lett, 1994, 72: 1706–1709.
[17] Han J H, Kim J S, Kim M J, et al. Effective vortex mass from microscopic theory. Phys Rev B, 2005, 71: 125108.
[18] Thouless D J, Anglin J R. Vortex mass in a superfluid at low frequencies. Phys Rev Lett, 2007, 99: 105301.
[19] Ao P, Zhu X M. Microscopic theory of vortex dynamics in homogeneous superconductors. Phys Rev B, 1999: 60: 6850–6917.
[20] Ao P. Motion of vacancies in a pinned vortex lattice: origin of the Hall anomaly. J Phys Cond Matt, 1998, 10: L677–L682.
[21] Zhu X M, Brändström E, Sundqvist B. Observation of the transverse force on moving vortices in YBCO films. Phys Rev Lett, 1997, 78: 122–125.
[22] Kwon C, Ao P, Thouless D J. Structure of stochastic dynamics near fixed point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5, 102: 13029–13033.
[23] Ao P. Laws in Darwinian evolutionary theory. Phys Life Rev, 2005, 2: 117–156.
[24] Ao P. Borges dilemma, fundamental laws, and systems biology. Bioinforma Biol Insights, 2008, 2: 201–202.
[25] Ao P. Equivalent formulations of ‘the equation of life’. Chin Phys B, 2014, 23: 070513.
[26] Ao P, Galas D, Hood L, et al. Cancer as robust intrinsic state of endogenous molecular-cellular network shaped by evolution. Med Hypotheses, 2008, 70: 678–684.
[27] Su H, Wang G W, Zhu X M, et al. Endogenous molecular-cellular network theory: a system-biomedical perspective towards complex diseases (in Chinese). Chin J Nat, 2015, 37: 448–454 [苏杭, 王高伟, 朱晓梅, 等. 复杂疾病的系统医学视角: 内源性网络理论. 自然杂志, 2015, 37: 448–454]
[28] Yuan R S, Zhu X M, Wang G W, et al. Cancer as robust intrinsic state shaped by evolution: a key issues review. Rep Prog Phys, 2017, 80: 042701
[29] Yuan R S, Ao P. Beyond Itô versus Stratonovich. J Stat Mech, 2012, 2012: 07010.
[30] Efimkin D K, Hofmann J, Galitski V. Non-Markovian quantum friction of bright solitons in superfluids. Phys Rev Lett, 2016, 116: 225301.
[31] Zhu X M, Tan Y, Ao P. Effects of geometric phases in Josephson junction arrays. Phys Rev Lett, 1996, 77: 562–565.
[32] Ao P, Zhu X M. Quantum interference of a single vortex in a mesoscopic superconductor. Phys Rev Lett, 1995, 74: 4718–4721.
作者简介
敖平,教授,重庆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赴美留学,师从A. J. Leggett研学物理,获博士学位,博士后进一步就教于D. J. Thouless。后转入系统生物,与L. E. Hood从事癌症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在从事物理、工程、生物、医学研究。
本文原文发表于《科学通报》2017年第12期,经作者授权发表于《返朴》,略有改动。
以上内容由办公区教程网摘抄自中国科普网可供大家参考!
标签: 科学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