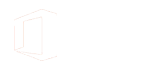清代天文学家李锐......
专访丘成桐(上):为了民族未来,一定要改变中国科学文化
今年年初,国际著名数学家、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教授做客由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信出版社主办的“父亲与我——谈《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线上直播活动。清华大学物理系楼宇庆教授在活动中采访了丘先生。
在本访谈文字稿的上篇中,丘成桐教授讲述了其父丘镇英先生虽然在自己14岁时就早早离世,但何以深远塑造了自己一生做学问、教书育人的底色,最终影响了自己的半生事业,也详细介绍了自己正竭力推动的数学领军人才教育的理念、做法和一些有价值的细节。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能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这位年逾古稀的学者对提升中国数学教育水准的赤诚和远志。
在下篇中,丘先生向学界介绍了自己在理论物理学和应用数学上的一些重要工作,并分享了关于数学和物理的一些独特看法。
此文是我们为了让读者更便捷地了解访谈的要点内容,根据直播实况并去除口语交流的琐碎,重新排布问答次序后重新归整编辑的文字稿,经丘成桐先生授权刊登。此次访谈结束后,丘先生还在线回答了观众提问,可参见《丘成桐对年轻人说的话》。已获得“返朴”长期白名单转载授权的媒体,如希望转载此文,请单独申请并等待授权。
注:此次直播共包含4个视频,分别是丘先生介绍《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楼宇庆教授访谈、丘先生回答读者提问。每个部分侧重点皆有不同。感兴趣的读者也可至《返朴》视频号合集《丘成桐先生的访谈直播》观看原始录像。
整理 | 谭莹、小叶
父亲何以影响我半生事业
楼宇庆:感谢丘先生接受我们的特别采访。我从不同的场合听到过您的演讲,能看出您的中文功底很深厚,这方面是您自身的兴趣所致还是父亲对您的影响,或是家庭环境的熏陶乃至学校教育的影响?您大二以后就去了美国学习和研究数学,还一直保持着对中国诗词和历史文化的兴趣吗?
丘成桐:我一辈子最喜欢数学,从数学出发,对物理和其他学科都有很大兴趣,所以我在物理上也做了一些还算重要的工作。在做数学和物理的时候,我喜欢宏观的看法,不单看一个小题目或者一个小方向。我认为所有重要的学科要完成真正重大发展,都是因不同的观点碰撞出来的火花,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
这也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一种看法。他教我诗词,教我古典文学,也教我哲学。哲学里边也不单讲中国哲学,他的兴趣是中国哲学,但是他认为要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从希腊哲学开始,一路到康德,到马克思。此外,还要考虑印度的佛教,佛教在中国有很重要的影响。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一路到魏晋南北朝,也影响到宋明理学,这都很重要。这些看法对我有相当的影响,我从小就觉得一门学问要从不同的方向来看,不但从现在发生的事情来看,也要从古典看到现在,每一门学问要看到源头,知道源头是怎么来的,才晓得它以后的走势。这些看法对我很重要。当然也要读历史,父亲教我历史,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也能让一个学者学习要怎么走,才能够达到最好的目标。做研究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有时候可能走不下去,取舍的问题就是很重要的。
要不要坚持做下去?很多学者都临门一脚了,但就进不去,不能够坚持,因为没看清楚;有些学者是坚持下去,做到了。这种种做法,其实跟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决断都有关系,有的临到一念之间走错了,就完全走错,有些走对了就完成了。这跟我们做研究很像,我们做一个大学问的时候,往往要靠自信心和欣赏学问的能力,能不能坚持下来,都跟我们的修养有很密切的关系。很多学生,尤其中国的学生,花了三四年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觉得没有前途了,就放弃了,但是往往在你要放弃的时候,其实走错了路。我一辈子做学问注意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对我影响很大。
我年轻做了几个重要决定,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是我人生转折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14岁时父亲去世,那时候读初三,面临要不要继续做学问的问题。父亲去世的时候,家里兄弟姊妹好八个,只剩下我妈妈一人要养这么多孩子,很辛苦,我要不要念书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我妈妈很支持我继续念书下去,假如我当时决定生活比学问更重要,就不可能做学问了,这是我第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不但要念下去,同时要念得很好。我小时候就很清楚,我父亲很希望我能够做学问,我相信我父亲,就有信心要做学问下去。但是做这个决定不容易,家庭很辛苦,家里面也需要我的照顾。后来,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决定。其中一个是大学读完时要不要出去,还是留在香港。我中学毕业时,台湾大学就期望我去那里念书,台湾的数学比香港好,但是我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香港,这种种决定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你也可以讲我运气很好,每一次做的决定基本上对我来讲都是好的决定。有可能走错了一步,就走到完全不对的地方去了,那一生就完全改变了。
这好几个重要的正确决定,都至少跟我父亲的教导,跟他对我在历史上的许多培养、看法都有很大的关系。
楼宇庆:您父亲希望您做学问,是说他已经看出您在数学方面的一定的才华,还是就是一般性的他觉得你应该做学问?
丘成桐:我父亲在我十一二岁时就开始教我做学问,教的是通学,譬如他教我文史、哲学。我父亲不懂数学,但他看得到我在数学方面有点天分。我父亲在我14岁的时候去世,根本来不及来指导我到底走什么方向,我很清楚他不但期望我做学问,同时做好的学问,这些学问能够有影响力,能流传下去。我始终记得我父亲对我的鼓励,虽然他没有直接讲,但从他的言行、教导里面,我晓得这是他的期望,他对我的期望很高。我母亲也晓得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很多事情也沿着我父亲的走法。虽然生活很辛苦,但她还是支持我继续念书,跟这个有密切关系。
父亲对我的教导包括文学教导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文化上的提升。我不会生活好了就满意了,而是希望我能够做些大事,很早我就有这个看法。
提升中国科学文化,须从初中着手
楼宇庆:一般人通常感觉数学很难,高深又抽象,尽管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有点区别。中华民族人口众多,按比例会有一定数量特殊天分的人存在。您现在在努力普及数学教育,选拔优秀人才,您觉得在中国怎么能鼓励、促进这群年轻人发展他们的才华,在数学上作出杰出贡献?
丘成桐:现在中国需要科学文化作为基础,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们看一些小孩子对科学有点兴趣,但得不到家长和老师的鼓励,他们鼓励的是高考考高分,奥数考高分。这种鼓励,让小孩子失去了对自然奥秘的兴趣,这一点是要突破的。我们要提升中国的科学文化,坦白讲只能够从初中开始,所以我现在对初中生有很大兴趣。
由于高考,大多数高中生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准备,差不多高三全年。初中毕业时有个中考,初中生也几乎也要把初三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准备。这是一个很令人担忧的现象,花整年的时间准备考试,不但让小孩子陷入机械式学习,慢慢也将他本来的兴趣磨灭掉了。最重要的是,孩子会认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就是考试,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了。这是很不幸的事,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改变这种文化,让至少一小部分,譬如千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改变。高考一年有1000万人考,千分之一也不少人了,或者哪怕只有万分之一也很好。培养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科学家或者学者,就能够改变中国的未来。我们一定要改变中国的科学文化,让孩子们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够改变中国科技发展的命运。
楼宇庆:您在清华大学开办了特殊的数学训练班,年纪最小的是初中生,可能只有13岁、14岁。我记得以前跟您聊的时候,您非常雄心勃勃,期待他们中间有人将来能够获得菲尔兹奖。那么您怎么选录他们?大致的培养计划和训练步骤是什么?他们还是挺小的小孩,您亲自给他们开课,适当的时候就向他们介绍数学前沿的问题,那么您也会同时也要求他们重视其他不同的学科,比如物理学吗?
丘成桐:我们很重视教育小孩子懂得不同学科,成为通才。我们这个班叫“领军班”,领军班是数学跟物理并重,考试的时候数学要考得好,物理也要考得好,基本上他们数学跟物理的能力都要达到大学一年班的程度,这是我们考试的规矩。我们要求学生不但数学跟物理好,同时也要求学生有能力去接受其他学科,比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求真书院每周有三个重要的全体演讲,一个是周一晚上我自己讲一个半小时数学史,为什么要讲数学史?因为在中国,一些中国数学家做的方向很狭窄,不够宏大。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们对数学的潮流以及古今中外的发展不大了解,缺乏培养通才的做法,所以我自己每周给他们讲一个多小时的数学史。
基本上,从古希腊讲到18、19世纪,我这周(编注:指2022年年末)讲到19世纪的数学家,预备要讲到20世纪的数学家。目前,我基本上讲了33个数学家的历史。这些历史对于小孩子很重要,他们会知道世界上好的数学家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怎样走出自己的路来。他们有不同的学习方法,有不同的成长过程,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样,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现在一般来讲,我们的学生读不懂这些。有时候对刚开始来的学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规定他们非听不可。
我讲容易的内容,他们很感兴趣。但是,不能单学容易的,有些内容是必须要有的。我不能讲很肤浅的历史,要讲一些有内容的历史。一定要他们晓得有这些事情,其它可以慢慢再学,至少在他们脑海里种下一颗种子,知道当年有学问的学者是怎么产生的。他们自己不懂得怎么做学问,要从伟大的数学家的经历里学习要怎么走这条路。我们寻找这些学生时,花了很多功夫遴选,要好好培养他们。从初中开始找这些学生,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但是小孩子总归年纪小,某个学问可能成熟了,其他方面并不是很成熟,我们要慢慢改进,但是要从一开始就发展这些认知。
刚才你问招生,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军计划每年不通过高考招收100个学生,很多家长就觉得不用参加高考是很伟大的事,但是他们误会了。我们要招的是很有兴趣念数学的学生,而不是冲着不用高考的学生。有些家长可能以为进了求真书院,之后可以转到经管去,因为进经管学金融才是他们最有兴趣的。但我们不允许学生进来后再转去学金融经管。
我们一开始跟家长、小孩都说清楚,来求真书院就是要念数学,学完数学后,你要去念经管我不管,但至少基础一定要打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我自己现在每周有大概10个学生在跟我研究数学,最前沿的数学。我带他们,他们虽然只有十七、八岁,但念的内容其实跟哈佛大学研究生一样,所以他们没有问题,都可以开始做研究了。我们讲最好的学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但是有些进来的时候水平还不够,还要训练他们。我觉得只要花工夫,都可以训练得好。但现在中国有个问题,照我来看是,老师怕学生,大学怕老师,都不希望出事。
举一个例子,我要规定他们念数学史,他们觉得其他学校不念,为什么我要念,我不想念。别人不念,而我要规定他念,他们觉得不高兴。孩子总是爱玩,觉得玩的时间不够。
楼宇庆:您讲数学史,给学生们讲了相当多的数学名家挫败或成功的故事,这对于数学教育非常重要,类似的故事在物理学里也同样很重要。这些研究过程中的契机以及人在那一时刻怎么把握等等,您能在这方面再讲一些吗?
丘成桐:在数学史上,从伟大的阿基米德开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对学问的态度,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笛卡尔、莱布尼茨或者牛顿都有各自的长处。我想,将一个好数学家真真实实的生活跟他们的看法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事,现在媒体里描绘的数学家或者其他学科的学者近乎毫无瑕疵,每一个学者都很完美,其实完美的学者并不存在。比如莱布尼茨就跟牛顿吵架吵得一塌糊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牛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但是牛顿跟两个重要的人吵架,一个是莱布尼茨,一个是胡克。有可能牛顿对他们并不很公平,但牛顿还是伟大的,没人能够否认这个事。高斯也跟人吵架,高斯有很多没有发表的研究,但别人做了,高斯就讲是他先找到的,种种情况都有。对有血有肉的数学家,我们要晓得他们的看法,并不表示我赞同他们的看法。但是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晓得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不用避讳。
有一点很重要:每一个伟大数学家都对数学本身抱有很大的激情,这一点无论如何避不开。一般来讲,从十三、四岁就要开始将他的数学能力培养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子,他们刚好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就应当将他们的数学热情提升起来。
第二点,我们看历史上所有数学家,他们都跟某些大数学家有接触,无论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以后都跟他们有接触。连阿贝尔都是这样,他出身贫穷,之所以后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到巴黎跟好几个大数学家有来往。我要学生晓得,你要接触的是伟大学者,能够跟他们有些来往,要了解他们的著作,没有一个学者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的。如果学生不晓得这些的话就很麻烦。学生们一定要看名著,要看前人用的方法,我教学生数学史就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你不一定听得懂内容,但是你会晓得一种不同的整体氛围。
想想看,假如你生长的环境里有33个数学家就在你旁边,你天天跟他们来往,通过历史来交往,你的境界就慢慢提高了,看得就远很多,不会斤斤计较一些小问题。因为你到那个境界后,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小东西,你要追求的是更高、更有意义的一个境界,我们要将学生带到这样的境界里,才能够走出一条路。做物理也同样,麦克斯韦很伟大,他一开始对电磁就有很大的兴趣。我下礼拜可能讲玻尔兹曼,他对统计物理很有兴趣。每个大学者有种种不同的成长经历,有些人活得很痛苦,而有些人出生就是贵族,各自成长经历不同,我们要能够了解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像伽罗瓦,20多岁自杀了。根据我的了解,他不是一般人讲的为爱殉情,是法国大革命激起了他很多压抑的情绪,最后决定要去死。刚才讲的阿贝尔,也在伽罗瓦的工作上做了很多,也是26岁就去世了,他们都是伟大的数学家。我们今天要知道他们年轻时走过了什么途径,他们的想法为什么可以影响至今,他们曾看得很远,我们学生们要能够懂这些。
年轻英才如何青出于蓝
楼宇庆:我记得您曾特别提到在伯克利读书的时候,有一位Charles Morrey教授讲课,讲到最后好像可能就剩您一个人了,是不是?但他还是非常认真地备课。
丘成桐:对,Charles Morrey是伟大的数学家,当时伯克利除了陈先生以外有几个伟大的学者,一个是Charles Morrey,一个是Stephan Smale。Smale教拓扑学,Charles Morrey教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当时我跟他的时候,我根本不清楚他是什么学者,但是我听他的课越听越有意思,他是哈佛毕业生,是非线性椭圆方程方面最伟大的一个学者,做了很多重要工作。我慢慢跟他学习,越学习越佩服他。他基本上没有学生,但是我跟他跟得很近,因为就是你刚才讲的,最后他班上只剩下我一个学生。就算这样,他还花工夫去准备,带着我去伯克利图书馆找书、参考文献。他对我很好,我也很佩服他,他真是个伟大的学者。他本来想要我做他的学生,他一辈子没有学生,期望我做他的学生,但当时我已经决定要师从陈先生了,就不好改变了,否则我可能就做他的学生,因为我很佩服他,他的学问也影响了我的学问,影响了一辈子。
楼宇庆:像伯克利这样非常好的学校,这样非常好的学者,一辈子没有学生,他的同事会有点议论吗?
丘成桐:伯克利老师那么多,有些人比较懂得讲话,有些人教的内容容易学,学生还是愿意去学那些容易学的东西。Charles Morrey是一个很老派的学者,平时上课还戴个领带,跟伯克利格格不入。因为伯克利的校园气氛很嬉皮士,很松散,而他是老派的哈佛大学来的大教授。从生活上来讲,学生不大喜欢这种老师。同时他很严格,每次上课的时候,叫学生上来讲自己懂不懂,还会布置一些问题,下礼拜学生要上来答,结果学生都怕他,不敢答,只有我愿意答题,所以他对我很看得起,就是这个缘故。
他做这种学问是要花很多工夫的,作业特别难啃,要验算很多东西的。当时同一个时期,其他的学派,不用花太多工夫就可以写一大堆文章,所以学生比较喜欢容易做的东西。但Morrey是很伟大的学者,这绝对没问题。
楼宇庆:我想起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李政道、杨振宁当年他们都是选了钱德拉塞卡的天体物理课,当然是很理论的课程,传说中最后也是剩下没几个人,恐怕就是他们两个人了,所以似乎这有一点类似。钱德拉塞卡也依然非常认真地备课,而且还会开上两三个小时的车到芝加哥大学来给他们俩人上课。
丘成桐:钱德拉塞卡我认得,我做彭罗斯那个问题的时候在芝加哥,他邀请我去演讲,他当时觉得很好。钱德拉塞卡也是一个老派学者。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在芝加哥跟他有些交流。
楼宇庆:在清华,学生有时候会觉得您要求太严了,就像当年伯克利Morrey教授的课那样。像您这样年轻时有强烈的研究兴趣,又碰上好的老师,无疑是一种最佳状态,那么您现在在清华,有没有一两个您觉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您,一直非常认真执着的学东西的孩子?
丘成桐:这是个很好的比较。当年我在听Morrey课的时候,很多学生离开了。Morrey先生很有意思,他有一天谈到教学评估——就是学生评论教员的教课水平——他自己是排在最后面的。整个伯克利差不多一百个教授,他在最后。后来他跟我讲,他排在最后并不重要,很多学生对他不满意,因为听不懂他的课。但是有一个学生能够了解Morrey的功力,同时学了不少就够了,像我就愿意学他。我认识的从事这一行的朋友,每个人都很佩服Morrey先生。所以Morrey也不在乎有些学生说他的课是教得最差的。对我来讲,我们求真书院不止有一个、两个,而是有一群很好的学生,他们都愿意学。同时他们根本不认为太难,也不因为有太多东西要学而厌倦,他们有能力,有兴趣,所以我很欣赏他们,我觉得我们能成功。但是其中也有几个学生觉得课业太重了,就抱怨。这事我不在乎,我为的是他们好,他们不想念是他们的事。我挑学生,挑第一流的学生,不可能每一个学生都适应同一类的教法,总有一些学生会觉得不行。
楼宇庆:您能介绍一下陈省身先生对您的影响吗?我记得您在书里讲过当时Stephen Salaff 在香港帮助你去申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您当时一直在尝试卡拉比猜想,陈先生建议您去尝试黎曼猜想,但您还是坚持选择了卡拉比猜想,最终成功了。请问在今天,如果您碰上很聪明的年轻人,您会鼓励他大胆去尝试解决比如像黎曼猜想的这样的很难的问题吗?还是要采取一定的策略,选择一些相对容易一些的?
丘成桐:首先第一点,陈先生对我的影响其实很早。我读初三的时候,就是我父亲刚去世没多久,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是陈先生写的,叫做《学算四十年》,这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根本没有听过陈省身先生的名字,当时国内最出名的数学家是华罗庚,其他人我都不知道。知道华罗庚是因为我们这边报纸会常常提起他,同时我也看过华先生的书,华先生写了很多通俗科普书。
但我看了陈先生的文章以后,才晓得陈先生在伯克利是大教授,在数学界已经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数学家,这点对我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直到我父亲去世以前,我听我父亲讲的大有学问的学者都是外国人,尤其是理论科学家都是外国人。当我看到陈先生这篇文章以后,我才晓得中国数学家也可以在整个理论科学里举足轻重,中国数学家也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这是陈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至于去伯克利,最先提拔我的是从伯克利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我,就是斯蒂芬·萨拉夫(Stephon Salaff),他认为我做得很好。萨拉夫将我的名字给了当时伯克利的一个教授,跟他讲我是很好的学生,大学就收了我。当时我跟陈先生没有来往,因为我不晓得怎么跟他来往。伯克利收我是没按常规的,我那个时候大学三年级还没毕业,没有拿到学位,伯克利就要收也不是容易的事,虽然可以走得通。但是照我看,当时伯克利一定拿了我的卷子去问陈先生,陈先生是当时伯克利唯一的著名华裔数学家,所以他们一定问他。
同时陈先生在伯克利的数学家里边是主导的,可以说当时是他在搭建,所以他一定也看过我的卷子,同时也一定赞成收我,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到伯克利以后,第一年其实陈先生在学术休假,那时候我跟其他的教授多一些来往。
到了我去伯克利那年的圣诞节,我自己做了一些几何方面的文章出来,当时刚好对几何开始有兴趣,这个文章还有点意思了,到现在还是蛮不错的文章,也发表到一家很重要的杂志。那个时候还写了一些其他文章,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过了几个月以后,我又跟伯克利其中一个博士后一同做了些文章。陈先生休假回来也很高兴,首先我是一个华裔学生,他觉得提拔我没错。
他看到我就很高兴,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请他做我的导师。当时他讲要做黎曼猜想,但是我对于黎曼猜想兴趣不是很大,直到现在我还对它兴趣也不大。我对于我想做的事情兴趣大得多,就是卡拉比猜想,我认为卡拉比猜想,至少在我的个人品味来看,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花全部的精力在做那个事情。黎曼猜想值不值得做,要看个人的喜好,就是品味,假如他没有这份兴趣,那就不用做,不要为了一个出名的问题来花很多工夫。但假如一个人真的发觉自己有这个兴趣,有一定的想法,我倒会鼓励他去做。
我这一辈子也是这么做的,从来不会因为某个问题出名我去做,就像卡拉比猜想,我是因为它整个结构跟想法很漂亮,同时能够影响整个数学的基础。我当时为什么这么看重卡拉比猜想?因为它不但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对整个几何学基础会产生很重要的改变,这让我很兴奋想去做,解决之后果然是这样。
拿不拿奖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希望我们的学生也能够这样子,不要为了拿奖、出名而做学问。现在在中国,坦白讲,最糟糕的问题是,有才华的学生,为了拿“帽子”,为了做院士来做学问,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做学问,不从对学问本身的兴趣和问题是否漂亮出发,始终做不到第一流的学问出来,也没有自己的看法。做一个伟大的学者总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没有自己的看法是不行的。

《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丘镇英著,丘成桐编;中信出版社(2022年10月)

《大宇之形》,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1月)
本文受科普中国·星空计划项目扶持
出品:中国科协科普部
监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以上内容由办公区教程网摘抄自中国科普网可供大家参考!
相关文章